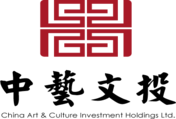辽上京遗址考古现场探访记
2016-08-26 12:58:36 作者:单颖文 来源:文汇报 已浏览次
2011年起,辽上京考古队开始了对中国北方第一座草原都城“辽上京”的系统发掘。考古队今年的工作重点,是对宫城南门遗址进行考古发掘,探寻上京是否存在从东向向南向轴线转变的过程。
“上京,太祖创业之地。”《辽史·地理志一·上京道》中这样写道。辽上京,中国北方第一座草原都城,位于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林东镇东南。上京在辽代贵为五都之首,在金代继续沿用。后来,金人敌不过元军的金戈铁马,上京失守渐遭废弃。当繁华终归于尘土之下,这座建成于神册三年(918)的皇都,却于千年之后成为国内目前保存最好的古代都城遗址之一。
“辽上京保存得很好,但考古工作一直比较薄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辽上京考古队领队董新林告诉记者,从2011年起,在每年适宜当地考古发掘的6月至10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二队和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组成的辽上京考古队,就会驻守辽上京地区进行系统发掘。其中,2012年对辽上京皇城西山坡佛寺遗址的发掘,还荣获了当年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面对辽上京这座富矿,董新林说,他曾计划在此发掘30年,“但其实做50年或更长也不为过,都城的考古发掘是可持续的”。
本月初,“契丹辽文化暨第三届契丹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巴林左旗召开,董新林的辽上京近年考古发掘情况汇报,是最令人瞩目的报告之一。当时有学者对记者说,辽上京考古能取得现在的成绩离不开辽上京考古队,“如果换个队伍,或许未必能出这么多成果”。会后,记者三赴辽上京考古基地,真切体会到了此句绝非虚言,也见证了这支超强团队为这处遗址“申遗”所付出的努力。
探方里的车辙
在巴林左旗林东镇,辽上京遗址一般被当地人称为“古城里头”。这里的古城,并非只是行政意义上与“新城”区分,而是真有一圈夯土老城墙做了隔断:城墙外是楼房、商铺和喧嚣的市集,城墙内是树木围着沙地,间或能见到牧民在这里放牛和羊。出租车司机从城墙的豁口处开了进去。“然后怎么走?”他问道。“你就跟着地上颜色最深的车辙开吧!”当地资深文物研究者G先生答道。
路面上没几道车辙,有一道颜色特别深,而且一眼望不到头。G先生说,最深的这道就是人们去考古基地上班、参观轧出来的,其他一些浅的车印子可能是不久前附近村民自己开车来玩留下的。说到这,他看起来有些忧心忡忡:“最近老有人开车往城墙上冲,有一回我还看到有辆车翻在那儿。他们这是在玩儿吧,但是这既危险,又对城墙造成伤害,你们能不能给呼吁一下?”
正说着,眼前的沙地中出现了目的地。率先映入眼帘的,是一面写着“辽上京考古队”的鲜红旗帜。考古基地是片被1米来高的铁丝网围起来的区域,下了车推开铁丝网的门走进去,只见中间是四个10×10米的探方,戴着防风沙遮阳帽、太阳镜、口罩“全副武装”的考古队员和工人们在探方内外忙个不停。探方边停着辆印有“中国考古”红字的房车,还有个简易的临时工棚。
“这个探方的位置就是辽上京宫城南门区域。今年,我们的工作重点是对宫城南门遗址进行考古发掘。”董新林说,在去年和前年,考古队首先确认了辽上京宫城4面城墙的存在,并分别对辽上京宫城和皇城的东门遗址、宫城西门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在《辽史》记载和考古勘探试掘中,都未发现存在宫城北门),并有了重大发现:辽上京宫城、皇城的西门都是单门道,宫城、皇城的东门都是三个门道,由此可以看出,东门比西门的级别要高,这体现了契丹人尚东的思想;从皇城的东门到宫城的东门,延伸到宫城内的轴线上,发现有大型的宫殿遗址,这意味着首次从考古学上确认了辽上京存在东向的轴线。这与历史上多数帝都,比如北京故宫这样呈南北向中轴线规划的方式大为不同。“不过,辽太宗获得燕云十六州后,统治者的理念可能发生变化,辽上京或许存在从东向向南向轴线转变的过程。我们现在想通过对宫城南门的勘探和发掘,尝试能否从考古学的角度来解决这个大家关心的问题。”董新林说,“辽上京遗址考古的工作目标,就是要搞清辽上京城的布局、功能分区和历史沿革。”
董新林告诉记者,历史时期的考古工作需要通过实地踏查、考古勘探和试掘等,再结合历史文献来综合探寻遗址的地理位置。尽管辽代被称为中国历史上“第二个南北朝”,但《辽史》修得仓促草率,所以能够留给后人作参考的文献资料并不多。在《辽史·地理志一·上京道》中写道:“辽上京分南北二城。北为皇城,南为汉城。……城高二丈,不设敌楼,幅员二十七里。……其北谓之皇城,高三丈,有楼橹。”而其中,提及上京皇城中的“大内”,即对宫城的描述,仅寥寥数语:“……中有大内。内南门曰承天,有楼阁;东曰东华,西曰西华。此通内出入之所。”董新林说,在辽代文献资料比较少的情况下,越发凸显考古发掘资料的重要性,同时更加考验考古队员的细致和耐心。“稍不注意,就可能放过一个重要的现象,损失一份重要的实物资料。”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辽上京考古队队员汪盈把记者领到探方边:“你看,这里有两条车辙。”看着探方内深深浅浅的土,记者似乎看到了许多条“疑似车辙”,这可比刚才出租车司机找车辙难多了。“你蹲下来,从探方中间那堵没打掉的探方壁底开始看,是不是有两个看起来颜色有点深的陷下去的地方?沿着这两个地方延伸出去的,颜色略深一点的土,就是车辙。”在汪盈的循循善诱下,记者终于找到了两条毫不起眼的车辙。
“这你们都能发现!”记者惊叹道。“车辙内的土是后来淤的,略松软些,和周围比较紧实的路面土不一样。我们当时清理到这个区域时,发现有两三厘米深的地层比较松,等慢慢把这些地层清理掉,就露出了这两段比较硬的凹面,也就是现在看到的车辙。”汪盈解释道,“这里还是金代的地层。有车辙,我们就可以确认这里在金代的时候,是作为道路使用的。而且,还可以通过两条车辙之间的距离,判断当时车的轴距,也可以根据路面的松硬程度,判断当时车辆的使用情况。”
那么,为什么这里是金代的地层呢?“这是根据地层中夹杂的建筑构件和陶瓷残片等判断的。”汪盈指着探方中间的夯土墙告诉记者,这个夯土墙的剖面,凭肉眼就能看到一条条的夯实印记,有经验的考古队员能根据土层质地、颜色的变化划分不同地层,而后分层收集出土遗物,最后做出大致的年代判断。比如,眼前的这片夯土墙中,有的地方夹杂着一些砖瓦、陶瓷残片。在辽代和金代的砖瓦形制差别不大的情况上,就要通过有一定区别的陶瓷片来判断这属于哪个时代的地层。后一个朝代的地层总是叠加在上一个朝代之上的,辽代的东西在金代可能被沿用,但金代的东西绝不可能出现在辽代的地层里,所以如果地层中出现金代的遗物,那么这个地层最早就不早于金代。从现场情况来看,在金代的地层中,原本位于辽上京宫城南门的位置,出现了许多金代房屋的建筑残迹,考古队员们用白色笔标注上“F+数字”代表房址,在车辙的位置标注上“L+数字”代表道路。董新林说,由此可以判断,在金代时这个宫城门可能已经废弃,以至于金人都能在城门的位置上盖房子了。
在探方中央,有一片隆起的区域,汪盈说,这是之前勘探到的宫城南门墩台的位置。预计在8月底9月初,能够清理到辽代的地层。“到时候,最期待的是见到拐角,这样就能基本确定南门的位置和形制了。”8月17日,记者看到“辽上京考古”官方微博发布了一则消息:“你们这么认真,果真找到包边石啦!”在微信上,汪盈告诉记者,现在他们已经发掘到了辽代的倒塌堆积,清理到的是南门的包边石,也就是用来包南门墩台边用的石头和砖。找到包边石,一来说明城门保存状况比较好,可以由此确定城门的具体形制;二来说明建造城门时用了石材、砖瓦等比较好的建材,可以证明这个门的相应级别,也可以就此讨论建筑技术水平的进步等。
不过,现在要谈辽上京是否存在从东向向南向轴线转变的过程还为时尚早。汪盈说,勘探只能是线索,需要等到今年的发掘结束整理完遗物后,再与之前的发掘结果进行全面对比和研究,才能确认。“这几天还会不断有新现象的,请大家关注‘辽上京考古’微博噢!”
西山坡的佛头
离开宫城南门的探方区域,汪盈带记者驱车前往遗址中的制高点,位于皇城西南靠近西城墙的一处呈缓坡状自然高地,当地人俗称“西山坡”。记者爬上西城墙俯瞰全城,只见在遗址中心靠东的位置,有一片微微隆起的区域。汪盈介绍,那里就是记载中皇宫的位置。
她说,现在这样用肉眼看地表有没有特殊点,就是考古工作的第一步,即踏查。“不过,即使是一样的地点,不同的人看出来也是不一样的,经验越是丰富的考古队员工作者,越是能在踏查阶段掌握更多信息。”
收回目光,只见眼前有三个明显的凸起,中间一个大,旁边两个小。汪盈说,这就是获得“2012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辽上京皇城西山坡佛寺遗址。如今,这片区域已经回填,也就是在外表上恢复到了发掘前的样子。
爬上中间那个2米来高的大土包,顶面是对角直径40多米的平地。在大土包不远处,竖着一块石碑,上面写着“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日月宫”,为巴林左旗政府2008年所立。“日月宫”一词,最早出现在《辽史·太宗本纪》中:“辽天显五年,八月丁酉,以大圣皇帝、皇后宴寝之所号日月宫,因建《日月碑》。丙午,如九层台。”但在《辽史·地理志一·上京道》中,记者却没有发现任何关于皇城内有“九层台”和“太祖庙”的记载。此前,在辽上京博物馆参观时,1楼大堂中以辽上京遗址为模型制作的沙盘中,西山坡的这片区域也被放上了“日月宫”的小牌子。那么,这个区域就是传说中的“日月宫”吗?
“我们一开始也是带着这个想法进行考古发掘的。”董新林坦言,1962年,内蒙古文物考古队曾对辽上京城遗址进行了初步的考古勘探,认为这里是传说中的“日月宫”。但他又看到有资料显示,1950年代,考古前辈李文信曾和日本人一起上西山坡调研窑址,当时他们提出假设,认为此地可能是佛寺遗址。而随着考古发掘的深入,结论越来越向后者靠近。
时间拉回到2012年7月。汪盈记得,他们是从中间这座最高大的台基开始工作的。刚揭开表土,一些人像残片,鼻子、耳朵、脸颊就露了出来。于是,他们从台基中间开始,打了个40米长、2米宽的十字探沟。结果发现,原本以为是四方形的建筑底座,出现了一条斜边。“清理以后,我们发现这个建筑基址呈六角形。按照业内的常规判断,这是塔基的形状。而且,是由大型包砖夯土台基和台上建筑两部分组成的。”
汪盈说,再深入发掘,考古队员们在塔基东部清理掉一层坍塌物后,发现了一堆大部分完整的泥塑佛造像。这些佛造像的出土,再次印证了“佛寺说”。后来,这批佛像残件被送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做“实验室考古”。经过考古工作者的细心拼对,在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师生的协助下,现在已经修复了其中5件较为完整的罗汉塑像。根据台基上残留的柱础、砖墙和木炭痕等遗迹现象,以及佛像的发现位置,考古队员认为,这些佛像原本是摆在木构回廊中供人参拜的。在回廊中,还发现了一些金代的铜钱、陶瓷片等,说明这座佛塔直到金代仍被使用。
在塔基内,考古队员们还发现了许多东倒西歪的石柱,有的类似圆柱形,有的是柱状多棱形,长度为1.5米至2米,有的甚至更长。在石柱周围,还有一些散落的砖块。经过反复讨论,专家们认定,这些高低不平的石柱是作为特殊基础承重用的,而且在外面包了砖。如今,在台基表面还保存了两根树立的白色石柱。汪盈说,较短的一根石柱是依原位保存,较高的一根石柱原本倒在一边,后来根据考古结果复位扶正,这样暴露在地表上也可以起到一定的定位功能。
汪盈介绍,在塔基内部的东西轴线上,考古队员通过仅存的底层砌砖,发现这里曾有3个小室。在前室和后室进门左手侧,各有一个长方形的小室,残存的地面铺砖通向成排石条方向,很可能这里曾有右绕的双螺旋楼梯通道。“我们判断,这座塔是座可登临的楼阁式塔。它和南方的塔不一样,内部不是空心的,而是实心的砖构实体。”汪盈说,根据塔基对角直径达40米,参照与其底径相似的现存辽中京大塔(80.22米)、应县木塔(67.31米),这座塔基上可能也有这样规模的高塔。
这样高大的佛塔为何会不复存在?汪盈介绍,目前大致有三种推测:一是人为破坏,可能毁于元军攻城之际;二是雷电击毁,此说主要是因为被发现的泥塑佛像有火烧过的痕迹;三是地震倒塌。“现在没查到有文献记载,还没有定论。”
在这座大型塔基的南北两侧,对称分布着两个小土包。汪盈告诉记者,经过考古发掘,发现这两处也都是六角形的佛塔基址,可能原本有两座不可登临的砖塔。可惜的是,这两个基址都被“反复盗掘”过。汪盈记得,在南侧基址的地宫中,考古队员还发现了一捆手榴弹。经公安部门鉴定,这是日式手雷,说明直到近现代还有人在此进行盗掘。幸运的是,在北侧基址的盗坑中,发现了一件彩绘的石雕残块,残件后侧还附有玄武图。佛学专家认为,这可以认定为是一件舍利棺的残块,说明这个塔基内可能曾瘗埋舍利。更令人叹为观止的是,在“连修砌地宫的青砖都被偷走了”的北侧基址地宫,考古队员们竟然清出了砖痕!“砖痕也就是泥缝,土会比周围的硬一点。幸好还有这些砖痕,让我们可以复原地宫的原本形制。”汪盈说,在回填阶段,他们通过铺沙、放沙垫等方法,完好地保留下了这些砖痕。
“其实每次考古发掘后,我们都会进行保护性回填。这是考古工作者对遗址应该承担的责任。”董新林说,回填是更需要耐心和细致的工作,“遗址是不可再生的,我们对古人和遗址必须怀有敬畏之心。”
辽上京的那些年
在辽上京考古队没有进入以前,辽上京的遗址是怎样的呢?记者特地邀请了当地两位解放前生人,辽上京博物馆创始者老馆长金永田(1941-)、G先生(1948-)一同前往遗址,用他们的亲历记忆和民间传说,拼出辽上京的那些年。
在巴林左旗,一名黑车司机王师傅曾自豪地告诉记者:“辽上京遗址是全国古都里保存得最好的,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都很注意保护先祖的遗产,自己不住,也不让人进去盖房子破坏。”那么,辽上京真的没有人住过吗?
金永田说,辽上京城平面布局呈“日”字形,北为皇城,南曰汉城。皇城为宫殿衙署所在,为皇亲国戚达官贵族住地;汉城是汉及其他少数民族集居区,作坊遍布,商贸繁华。汉城于1922年设置村庄,在多年来农民生产活动中,古遗址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皇城地势低洼潮湿,又是废都,据说有鬼神守护,没人敢住。当地还流传着一个故事,说解放前有人开车从锡盟额吉淖拉咸盐到辽上京,见天色已晚便在城里宿营,醒来却发现自己躺在城外,“说明老祖宗不愿意别人睡在自己的地盘上,这么一来,大家就对这个地方更害怕了。”另外,1964年,国务院将辽上京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不允许在此建房,遗址得到妥善保护。
在G先生的印象里,1944年苏联红军援华进入林东时,曾在古城驻扎过一阵,“一来古城开阔,二来军人没那么多讲究。”直到上世纪70年代,都很少有人走进皇城深处。甚至在“文革”破四旧时,这里也没遭到大破坏。“草长得很深,鸟都能在草丛里孵小鸟了。”一年中最有人气的时候是秋天,由于当地缺煤,附近的村民会结伴来这里割草回去烧火用。
王师傅还告诉记者,“文革”刚结束那会儿,他常见隔壁家邻居大叔扛回家一麻袋一麻袋的铜钱,“都是在古城里头捡的,还有铜铃、马镫等好多宝贝呢!”那么,皇城里头曾经真的遍地是宝吗?
“没这么夸张。”G先生说,他听老一辈说,1920年林东镇放垦,很多人来这里挖柱础、块石等建筑构件去盖房子。944年,家里有老人见过日本人在这里挖出了很多绿色的东西,可能是琉璃瓦。
金永田说,1977年他调到旗文化馆文物组工作时,常发现有人在古城里扒砖、捡瓦和拉土。为此他起草了《关于保护辽上京等文物古迹的规定》等一系列文件和通告,由有关部门批准、印发、张贴,向大家宣传保护古城的意义和规定。不过,也有不少违反规定的人。他曾碰到一伙开着大卡车来拉沙子的人,他不让他们走,司机做出要开车撞他的样子,他仍站在车前不走,司机只好卸掉沙子把车开走。据他所知,1970年,辽上京汉城曾出土一窖铜钱,有 6万多枚,以唐宋钱币为主,其中有辽钱9种11枚,这是出土辽钱最多的窖藏。这窖铜钱在出土时,流失在民间一部分,绝大多数被文物工作者抢救回来,现藏于辽上京博物馆。前几年,在皇城东南部还有尊石雕观音像,现藏于巴林左旗一间私人博物馆中。
为什么现在这里很少能见到宝贝了呢?金永田说,在皇城和汉城中间,有一条河流,名叫沙里河,辽代称为潢水。为了保护古城,国家文物局曾出资在皇城南墙外修筑防洪大坝,但在1990年,上京地区爆发了百年一遇的特大洪水。皇城北端局部防洪墙被冲毁,放在原文管所的辽代石磨都被冲到很远的宫城区。本来古城里有两只大龟趺,一只后来被从河里“抢救”出来(现存于古城中),还有一只仍下落不明。“大量沙土随着洪水涌进皇城,原来地面所曝露的遗迹、遗物都被泥沙埋到下面去啦!”
两位先生互相补充道,除了自然灾害,辽上京遗址还受到了一些人为破坏。比如,1950年代,为了修建公路,有人在辽上京大内前的小山上开采铺路的碎石。1955年,当时的昭乌达盟政府要在辽上京城内修建公园,施工线都划定了。幸好1956年昭乌达盟搬走,这个公园才不了了之。1983年,福山地乡办了一个翻砂厂,为了熔化生铁而收购瓷碗片作催化剂,当地百姓就跑到皇城里头来捡瓷片,5分钱一斤,收来的瓷片在厂里堆得像小山,后来在化铁时都烧了。再如,1960年,修国家级公路303线,道路施工竟从北向东穿过古城,好在为了保护辽上京遗址,2013年国道303线移出了古城。
巴林左旗宣传部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几年,政府更加提高了对辽上京遗址的关注度,采取了许多措施来保护遗址,比如动迁了遗址附近的人家,还修建了仿古建筑配合今后遗址公园的建造。
文物网版权与免责声明:
一、凡本站中注明“来源:文物网”的所有文字、图片和音视频,版权均属文物网所有,转载时必须注明“来源:文物网”,并附上原文链接。
二、凡来源非文物网的新闻(作品)只代表本网传播该信息,并不代表赞同其观点。
如因作品内容、版权和其它问题需要同本网联系的,请在见后30日内联系邮箱:chief_editor@wenwuchina.com
月度排行
新闻速递
- 2021年度文物保护示范工程公布
- 李白《嘲王历阳不肯饮酒》诗稿考论
- 习近平: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
- 张同禄80华诞纪念典藏展开幕,景泰蓝《盛世同路》引...
- 为盛世献礼,与第一大党同路!景泰蓝《盛世同路》在沪...
- 国之重器景泰蓝《和平颂宝鉴》入藏敦煌博物馆
- 景泰蓝泰斗张同禄八十华诞纪念典藏展盛大开幕,《盛世...
专题视点MORE
原创推荐MORE
- 文物网培训中心
- 美好时光
- 大家鉴宝—老窑瓷博物馆公益鉴宝活动圆满举行
- 曜变之旅
- 菖蒲河园,一袭釉色染枝头
- 龙泉琮式瓶
- 盛世风袭北京城,金秋月览长安客(下篇)
- 阿富汗珍宝展之:石膏盘上的希腊神话
- 秘色出上林
- 阿富汗珍宝展之:恒河女神雕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