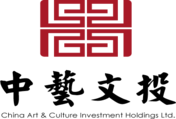杜柏贞:当代艺术语境中的历史性失忆
2015-11-22 21:57:52 来源:湖北书画艺术研究院 已浏览次
历史失忆症,似乎是长期困扰东西两方的当代状态。先讲西方在美术史和艺术批评的有关情况,早于2009年,福斯特(Hal Foster)已于《十月》(October)学刊指出,当代艺术貌似「游离于历史定位、观念定义和批评定论」,他进而提问:这种「游离」状态到底是真实还是虚构?它是否只是部分人的个人见解,还是「宏大叙事终结的直接效应?」-后者亦即后现代的困境1。面对福斯特的诘问,著名建筑师迈耶(Richard Meyer)就其观察所得,认为当代艺术「不只被视为处于超越/外在于历史的时间语境」,更甚者是,大部分当代艺术机构均「反对和压制历史意识」。因此他引用福斯特之言:「我们游走于美术馆的空间,仿佛它们是末日残留」2。姜苦乐 (John Clark) 从亚洲美术史的观点出发,在其著作《亚洲现代艺术》(Modern Asian Art, 1998)把当代形容为「历史缺席的场域」,并提问:「历史性失忆症的病因是什么?3它是否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病征- 把文化供求聚焦于最新近的时行风尚、最新的拍卖数额、最高的艺术品价位、最炙手可热的艺术明星,不断窒碍自省,为了那百分之一富人的利益,务求把销售和利润最大化?抑或这种历史失忆症其实来自异化的政治:领导阶层压制难以启齿的历史,以保全意识形态主旋律和统治阶层的诚信?又或者,历史的失忆症一如克拉所言,反映了「单纯的无知、相关知识的(直至最近才改善的)贫乏、对外和对外的种种话语偏见」?4。
不论背后成因为何,中国近代美术史学问的鸿沟正快速弥合。撇开过去二十年汗牛充栋的当代艺术著作,研究严谨、时段横跨十九世纪中期至当下的中国艺术专论,数量正显著增加5。反观美术机构对此趋势相当后知后觉,国外着眼于中国现代艺术的系统性机构平台付之阙如。中国国内类似的美术机构存在与否,确实是一大疑问,就算真有其物,它们的实际效率也成疑。在国外-主要指欧美 - 举目所见不过是一些着眼亚洲古物的美术馆(诸如大都会美术馆、旧金山亚洲美术馆、吉美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弗利尔美术馆等艺术机构),把过去十到二十年的亚洲艺术作品随意安插,意图赶上当今的艺术发展。实际上,没有西方美术馆认真和常规地讨论、研究自1850年至二十世纪末- 我称之为「现代」的时间段 - 的艺术数据。虽然这种情况的成因,可留待另一篇专论详述。但在此我亦不妨快语,其实把中国的现代性置纳于西方机构的语境,是深层的颠覆行为,不单打破「中国性」的本质主义话语,也威胁现存欧洲中心主义对「现代」的叙事。种种因素的结果就是明显的鸿沟,它让2000年前后横空出世的中国当代艺术之「非历史」印象千秋万代 。中国的美术馆的往绩亦不见彪炳 - 北京的中国美术馆、广州的广东美术馆、和近期开幕的上海中华美术宫不在此列。纵然我对这些机构心存崇敬,但恕我直言,这些美术馆的项目企划经常飘忽不定,同时因缺乏学术支持和对专业策展的专注而屡屡折衷、妥协。
盖因如此,M+正正为弥补这道「鸿沟」带来曙光。虽然冒着骑劫皮力的讨论会继而离题的风险,但我仍然希望藉由这次机会,在思考「水墨艺术在当代美术馆架构的位置」之余,同时探讨「现代艺术」在当代美术馆语境的境遇。我相信二者不仅相关,甚至可说是无法分割。在我看来,M+的目标和承诺是筑造展示和展览的平台,并将重心定位为讨论香港、中国和亚洲语境下,现代性的意义和多重历史。对于这些争论,水墨不但非风马牛不相及,反之,它更是这些讨论的核心,水墨艺术的存在和其持续实践,动摇了1)统一(亦即西方化的)现代性的假设和2)对全球化当代性的肯定。
在我把话锋转回M+的目标和愿景之前,得先申报本人和这个项目的私人关系。我曾与这次座谈会部分列席者一样,身为香港民政事务局于2006年委任的西九龙文化区的博物馆顾问小组委员,负责构思区内四所美术馆的前期发展计划。我在有关公务上的投入,经过多月来的发展,在2007年发展出一个另类计划。该企划建议建为M+建立统一的架构,包括目标宣言和初步愿景计划。我亦必须表明,是本人攻读中国美术史多年,一直保持对水墨美术的热爱,我那无数来自我们所讨论的那段时期的私人收藏可资证明。归结以上种种,你可以视我为「利益相关方」。
那我话说回头,话锋转回M+上。 虽说我在M+的同事对此谙熟之至,但为了自远方来的嘉宾,我还是要一再重申 M+美术馆的目标宣言,强调当中几个关键元素。作为文化机构,M+的主要焦点是香港当下视角中二十、二十一世纪广义视觉文化。M+一如大部分稳实可靠的文化平台,其特点应是高瞻远瞩、开放、跨范畴,并以教育和小区拓展为重。M+的项目企划和收藏在开馆初始阶段,将会先着眼于「四个主要类别」(民政事务处常以此名词称谓之)- 设计、活动影像、流行文化和视觉艺术(包括水墨)。
我要指出的论点,和上面的陈述一样简单明了。确立美术馆的分阶段发展花费多月的时间,过程涉及不少激烈争论。第一,请注意我们回避了「美术馆」一词,故此我看见此项目牵扯到这个词汇,不免颇为困恼。事实上,我们预期M+将会包含美术馆的部分传统功能 - 收藏、保存和展览,但它的目标却远不止于此,M+的加号也是从之而来。「加」究竟为何意?就是教育、研究、小区拓展和对话。事实上,M+中的加号,比象征美术馆的「M」更为重要。
第二,我们刻意规避「现代」、「当代」的字眼,因为它们负载太多,甚至过于西化。与其无条件地借用这些措辞,我认为M+提供了绝佳的机会,以讨论这些类别背后的种种假设,重新审视它们在香港、中国和亚洲各地语境下的重要性。我们认定二十世纪,或1900年左右开始的那个时段,是我们的出发点。从史实角度观察,滥觞之时从不是主要问题,它正正处于我们所见的机遇、还有亟待弥合的鸿沟的所在。是次座谈部分与会者建议开端应设在1950年,此前此举从未在考虑之列。故此也肯定了当代艺术确实需要历史语境。但实情是,我们也意识到收藏二十世纪上半作品的可行性,香港艺术馆早已收藏岭南画派和其它中国艺术的作品。香港部分私人收藏家也藏有二十世纪上至中叶的中国艺术佳作。他们会否愿意捐赠或长期借出这些作品?若然我们正在建立的是一所专业的国际级美术机构,我们希望他们对上述问题给予肯定答案。
我从以上论述引申到另一个观点的契机,是我们如何阐述「香港视角」?我们希望M+扎根于香港,希望它与香港人有所关联,并与港人互相共鸣。我们要求M+未来的策展人在企划收藏和艺术项目时,考虑到香港自身的独特历史轨迹 - 其滥觞绝非巧合地稍早于1900年。与此同时,我们也期望他们从当下的视角作出决策。所谓「当下」,或许正是M+运作宗旨中最悬疑未决但又最深具潜力的一方面,也是那些高瞻远瞩的艺术史学者和艺术评论家认为深具有批判性的要旨。首先,M+从不是当代视觉文化美术馆,毋宁说它是永远处于当代的文化机构,它的部分收藏可能来自转瞬即逝的当下,但它同时抱持这样的观点:当下注定于弹指间成为过去,成为久远往昔的一部分。出于这样的概念,M+有责任甚至义务通过「当下」的棱镜,以每天的新经验,不断更新对过去的理解。权美媛(Miwon Kwon)曾支出当代艺术「或许属于现时,但能重新激活过去」,这样的陈述,令我们重新思量我们已有知识(或者我们认为已知之事)。同样地,她认为『当代艺术历史在解/构/建构「当代」、「艺术」和「历史」』、「抛开艺术作品的生产日期,而着眼于其生命」6 之际,即达致其最佳状态。「艺术」和「历史」有相类之处,「留意艺术作品存在的环境,不管作品原本创作于何时」7。顺着相关的学术脉络,毕索普(Claire Bishop)曾警告道,若当代美术馆不「把握今时今日的重要议题、并同时急迫地、辩证和创新地审视过去」,它们或会沦为「向那1%富人颁授荣耀的神殿」,其馆藏无异「一堆美学残骸 …一直伸展往天际」8。
以上情况对水墨的处境究竟意味着什么?实际上,我相信它把水墨置于各种事物的中心位置。水墨的定位确实是西九龙文化区美术馆顾问小组多次冗长会议的争论重心。为什么?个中原因是水墨艺术本身有其独特的颠覆性,以致牵起极多正义。水墨艺术到底是否现代、进步,它是否与社会相关?它是否保守,甚至迂腐、本质主义、排外、易于因追求狭隘的民族主义目标而受落后政体的操控?水墨是否当代、清新、具前瞻性?抑或它是古玩爱好者的理想,与现今鼓励创新、批评和社会参与的话语毫无联系?水墨的运用明显不是全球性的,但它是否一种反抗、一道抵抗西方文化霸权同质浪潮的壁垒?水墨是否注定绝种的隐士式艺术实践,跟它所身处的社会毫无瓜葛?水墨是否只是媒介,抑或是一种思维?
重阅姜苦乐最近的文章,让我洗刷了对他的旧印象,此前我以为他深信水墨艺术大部分是非现代,甚至反现代的。反观安雅兰(Julia Andrews)和沈揆一的对此态度倒是比较正面。古根汉美术馆1998年的展览「危机中的世纪」(A Century in Crisis) 展出二十世纪的中国艺术,二人在该展览的相关画册和上月出版的著作 《现代中国艺术》(The Art of Modern China)均对水墨前景采取乐观态度。根据我对当代艺术的个人经验,至少对我来说,水墨艺术确实正在息微。中央美术学院近期展览「CAFAM未来展」就是此论点的例证。不管是无心插柳还是刻意为之,云云九十五位参展艺术家中,只有两位的作品和水墨具相类之处。
正是此状况把我引导道皮力提问的第二部分,即水墨艺术和中国先锋叙事。我得承认本人一向对「先锋」一词存异,事实上我甚少把此词与中国当代艺术扯上关系。毋宁说,借巫鸿的提示,我倾向采用「实验」一词,来形容游离既定常规以外的艺术实践。而且我不太愿意过分强调「八五新潮」在水墨艺术发展担当的角色,因为不管在当时还是现在,我始终不太信服八五新潮的某些知名人物确是该艺术运动的直接参与者和承继者,虽然我还是衷心期待皮道坚教授和鲁虹教授的论文陈述。我最深重的忧虑,是如果把水墨实验发展,归因于中国大陆的单一艺术事件,那台湾的刘国松(1932年生)、余承尧(1898年-1993年)、于彭(1955年生)、袁旃(1941年生)、许雨仁 (1951年生);香港的吕寿琨(1919年﹣1975年)、周绿云(1924年 -2011年)、王无邪(1936年) (见图1)、石家豪(1970年)该如何自处?这样的名单,我可以一直口若悬河讲下去。
纵然如此,诸君请千万别误会,我并不低估八五新潮在中国大陆语境的重要性。事实上那是一个值得注目的时期。正因如此,我们需要有更多有关它的原创的研究 - 尤其是对照、对比的研究。试想象一下,如果对比八十年代和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初这两个时段,到底能发掘多少出定夺前者功过的新锐观点。就我看来,八十年代不只是复兴发自五四运动的、尚未完成的现代性进程,它也挪用五四革命的部分形式。它们之间的共同点,不只在社会责任、自觉的历史主义、乌托邦梦想和令人振奋的理想主义,也表现于它们的启蒙导师、自发艺术组织、DIY-展览、手写宣言(例如:倪贻德(1901年﹣1970年) 1932年为《决澜社宣言》撰写的序言,有如出自毛旭辉(1956年生)手笔)和对西方现代主义风格的青涩实验。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读书热」中的那些影响深远的西方哲学译本,和更早的那个时代遥遥共鸣。那些书籍的封面,和二三十年代的平面设计互相对应。中国或许早有学者做过这样的比较研究,但我认为研究结果仍然充满多样的可能性。
既然有这么多局部的故事仍未绽露,既然我们需要地域之间的对照,为什么不稍稍反抗一下统一叙事难以抵挡的诱惑?比方说,全面的香港历史、香港与中国、台湾之间的透彻对比和研究,至今还尚未有人完成。更遑论把眼光伸延至中国以外,把香港和亚洲其它地区- 韩国?日本?印度更是不用说了 -作比较研究。这模拟较和观照,既然可以以书本的形式开始(请参考姜苦乐著作《亚洲现代艺术》(Modern Asian Art),为什么不能以展览的形式继续?历史比对实际上协助我们超越东/西、传统/现代、冲击/反应的简化二分法- 它们正是框限二十世纪艺术大部分讨论的元素。为了另辟蹊径、超越「西方逻各斯中心本质主义」的现代主义定义,- 正像皮力最近撰文所述,调和他所指的「外部批评」和「内部批评」-我们的思想范畴必须扩阔9。我们需要回首过去,同时从旁参照文化空间,我相信这是水墨(和所有本土艺术形式)在当代美术馆的位置至为重要之处。戮力调合外部与内部批评,不是什么新鲜事,也不是中国独有。刘海粟(1896年﹣1994年)、徐悲鸿(1895年﹣1953年)、林风眠(1900年﹣1991年)、丁衍庸(1902年﹣1978年)、关良(1900年﹣1986年)、石鲁(1919年﹣1982年)和他们在印度、日本、东南亚的同道人,早于二十年代已然开始了这种调和。
因此我希望,如果我们「准确把握当今的重要议题」、「以当下激活过去」,我们或许能在治疗历史失忆症的路途上踏出一小步。正如姜苦乐所言,「亚洲各国文化的现代性,各有其独特历史,此历史对当代艺术实践的各种发展举足轻重。假如二十一世纪确有将来,那十九、二十世纪就是其过去」10。这是M+抱持的宗旨,也是它的承诺。
责任编辑:小萌

文物网版权与免责声明:
一、凡本站中注明“来源:文物网”的所有文字、图片和音视频,版权均属文物网所有,转载时必须注明“来源:文物网”,并附上原文链接。
二、凡来源非文物网的新闻(作品)只代表本网传播该信息,并不代表赞同其观点。
如因作品内容、版权和其它问题需要同本网联系的,请在见后30日内联系邮箱:chief_editor@wenwuchina.com
月度排行
新闻速递
- 2021年度文物保护示范工程公布
- 李白《嘲王历阳不肯饮酒》诗稿考论
- 习近平: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
- 张同禄80华诞纪念典藏展开幕,景泰蓝《盛世同路》引...
- 为盛世献礼,与第一大党同路!景泰蓝《盛世同路》在沪...
- 国之重器景泰蓝《和平颂宝鉴》入藏敦煌博物馆
- 景泰蓝泰斗张同禄八十华诞纪念典藏展盛大开幕,《盛世...
专题视点MORE
原创推荐MORE
- 文物网培训中心
- 美好时光
- 大家鉴宝—老窑瓷博物馆公益鉴宝活动圆满举行
- 曜变之旅
- 菖蒲河园,一袭釉色染枝头
- 龙泉琮式瓶
- 盛世风袭北京城,金秋月览长安客(下篇)
- 阿富汗珍宝展之:石膏盘上的希腊神话
- 秘色出上林
- 阿富汗珍宝展之:恒河女神雕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