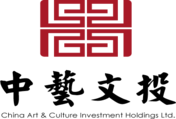末代大儒书院梦:马一浮与复性书院
2015-03-19 11:50:09 来源:腾讯儒学 已浏览次
楔子:侧身天地更怀古
一个多世纪之前的1905年,也就是清廷下诏废除科举取士,改设新学学堂的那一年,发生了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有一位二十三岁的青年,五短身材,其貌不扬,孤身一人来到浙江杭州,寄居在西湖边的一所寺庙中。他来杭州,是为了去杭州著名的“文澜阁”藏书楼通读浩如烟海的《四库全书》。在西学东渐蔚然成风的历史背景下,此举显得颇为不合时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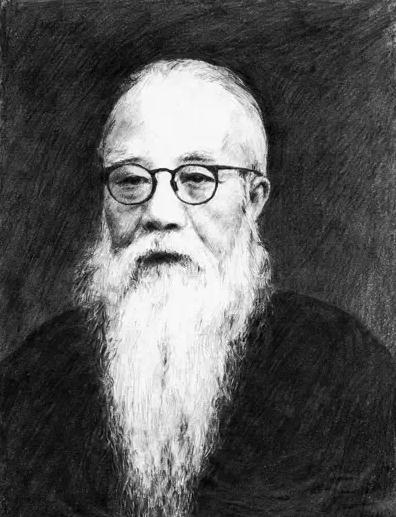
马一浮
然而,此人并非不识天下大势的井蛙,也不是因循守旧的陋儒。他年纪轻轻,已经创造了一段常人难以企及的辉煌:1883年,他出身浙江绍兴的诗礼世家,自幼天资过人,学业卓异,十六岁时参加县试一举夺魁,从此名闻乡里(鲁迅、周作人兄弟同时与试,都考了三十几名);随即,他被浙江名绅汤寿潜看中,招为乘龙快婿,抱得美人归;翌年,他到上海改学西学,又很快学有所成,几年后便精通数门外语,和朋友办报宣传西方思想,成为领时代风气之先的弄潮儿;1903年,他因英文优异被聘为清政府驻美使馆的职员,到美国圣路易斯市任职,后来又去欧洲游历,沐浴欧风美雨,遍窥西学典籍,甚至开中国人研读马克思主义之先河。
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正当文化界期待这位青年才子以更嘹亮的革命号角刷新故国视听时,他却放弃了一切西学上的计划,来到杭州的孤山之畔,推开了文澜阁的大门,重新捧起了落满尘埃的线装古书。一个洋装笔挺的新派青年消失了,许多年后,古老的藏书楼中,走出了一位长须飘然的国学大师、书法名家。经过一番痛苦的思想剧变,他在传统儒学的怀抱中新生了。
他原名马浮,字“一浮”,后来遂以字行。从1905年到1937年,从二十多岁到五十多岁,粗茶淡饭,读书练笔,成为他生命的基调。他在杭州寺庙或陋巷的隐居生涯中,把生命的盛年用于对儒学渊深精纯的追求上,因而被后人称为“隐士儒宗”。
一.扶老谈经兵乱后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马一浮由儒入道,由道入佛,又由佛返儒,出入三教,吐纳六经,学问日深,书法日精,名声也越来越大。知识界渐渐听说,在杭州有一位会通中西、平章华梵的马一浮,是当代首屈一指的大儒。苏曼殊、李叔同、丰子恺、梁漱溟、熊十力、汤用彤、宗白华等许多当时或后来的文化名人都曾向他问学。李叔同的赞语后来一直被人传诵:“马先生是生而知之的。假定有一个人,生出来就读书,而且每天读两本,而且读了就会背诵,读到马先生的年龄,所读的还不及马先生之多!”据说,1918年李叔同的弃世出家,就是受马一浮的影响所致。
然而和同时代的大多数知识分子相比,马一浮的生活却异常平静,既没有罗曼史的爱情,也没有卷入任何政治漩涡,甚至从未参与知识界的几次大论争。直到抗日战争爆发,他的生活才发生了巨变,走上了历史的前台。
竺可桢和马一浮相识于1936年,那时竺可桢刚出任浙大校长,登门拜访马一浮,请他出山在浙大任教,被拒。1937年,日本侵华,竺可桢再次恳请马一浮出山任教,说当此国家民族危急存亡之际,更应当保存命脉,弘扬国学。马一浮觉得,民国以来,非儒疑古思潮盛行,中国文化精神逐渐沦于虚无,而目前这场面临亡国灭种危机的大变局,或许正是中国文化复振的一大契机,于是破例同意到浙大担任“特约国学讲师”。
1938年4月,马一浮一行辗转来到浙大临时校址所在的江西泰和。随即,马一浮开始了两个学期的“国学讲座”。浙大方面对马一浮的讲座十分重视,竺可桢、梅光迪、苏步青等名教授都来听讲。颇出人意料的是,马一浮并没有一开始就一连串“子曰诗云”,他是以这一番话开场的:
昔张横渠先生有四句话,今教诸生立志,特为拈出,希望竖起脊梁,猛著精彩,依此立志,方能堂堂正正做一个人。须知人人有此责任,人人具此力量,且莫自己诿卸,自己菲薄。此便是“仁以为己任”的榜样,亦即是今日讲学的宗旨,慎勿以为空言而忽视之!
这一番掷地有声的话震动了在场所有的人。马一浮接着逐一解说张载的“四句教”:“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推陈出新,层层深入,又返本归源,时而雷霆万钧,当头棒喝,时而春风化雨,循循善诱,在座者无不叹服。马一浮以他的德操和学养征服了浙大的师生们。
就这样,马一浮在浙大开始了他一生中唯一一次的大学讲学。他的课程时间也十分特别,不按常规分星期,而是固定在每月的五号、十五号、二十五号,风雨无阻。因为“五”是《尚书·洪范》中的“皇极”之数,马一浮以为能够体现儒家的中庸之义。一个学期后,战火波及赣北,浙大又迁往广西宜山,马一浮在宜山继续了一个学期的讲学。后来这两个学期的讲稿遂被辑成《泰和宜山会语》出版,影响了几代学人。
二.春入巴渝草色寒
马一浮并不想在大学久居,他真正向往的是古典式的“书院”。中国的书院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它兴起于民间,与政治权力保持距离,朱熹、陆九渊、王阳明等大儒都曾在书院讲学,正是体制独立、学术自由、学风淳厚的书院赋予了他们的思想以长久的生命力。晚清以来,随着西式教育的兴起,书院也被废止。马一浮对此甚为抱憾,早年以来,他就想要成立一所融会中西文化的“通儒院”,“聚三十岁以下,粗明经术小学,兼通先秦各派学术源流者一二百人”,不但研习传统学术,也要兼通西方语文,延请中外学者分别指导,这样“庶几中土学者可与世界相见”。按他的设想,这种新型书院,本身是从传统书院制度中生长出来,又吸收若干西方教育的长处,将成为中西文化会通和发展的制度基础。
这个理想一度似乎有了实现的机会。1912年,辛亥革命后新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的蔡元培素闻马一浮的才具,写信给他,请他出山任教育部秘书长。马一浮欣然应允,前往南京赴任。到了之后才发现自己的想法过于天真:民国政府规划中的未来教育完全是欧式的,创立“通儒院”更当是天方夜谭。马一浮坚持“经不可废”,却得不到蔡元培的支持,半个月后即辞职。这是马一浮一生中唯一一次以失败告终的“出仕”。
马一浮痛苦地认识到,他曾经向往的革命不只要推翻一个清廷,而且也要打倒数千年的整个中国文化传统。儒学经典的崇高价值,在自由民主的意识形态下,将被彻底消解。唯一的选择是退回民间,在官方教育系统之外保留一点传统儒学的种子。
1938年底, 一个难得的契机出现了。抗战以来,不少马一浮的朋友和弟子在重庆活动,倡议成立书院,最终竟传到了蒋介石的耳中。很快,国民政府拨了一笔款项,作为创办书院的基金,由行政院院长孔祥熙发电报到宜山请马一浮入川主持。马一浮特别强调说:
书院之设,为专明吾国学术本原,使学者得自由研究,养成通儒,以深造自得为归。譬之佛家有教外别传,应超然于学制系统之外,不受任何制限。
为此,马一浮提出,书院的经费必须完全是来自社会捐赠。政府拨给的款项,仅被视为一种社会性的捐款,以保证不受官方的干涉。在他看来,书院必须独立存在,如果有国家权力的参与,必将转而为世俗的政治目的服务,书院的根本宗旨也就失落了。
这些要求,国民政府都表示同意,并允诺“始终以宾礼相待”。于是1939年春,马一浮经贵州入蜀。半个世纪以前,他出生于成都,幼年也在蜀中度过,此番故地重游,不禁悲欣交集,沉痛、感伤、希望、焦虑和决心一时俱涌上心头,融入了随口吟出的诗句之中:
平怀忧乐觉天宽,危栈盘纡识路难。
野老争言兵后恨,乱山都在雾中看。
地经骆越人烟少,春入巴渝草色寒。
万里萧条长极目,残年敢计一身安。(《自桂经黔入蜀道中述怀》)
马一浮到重庆后,受到了官方的隆重接待。蒋介石亲自宴请,宴会结束后,还特意把马一浮拉到一边,说素来仰慕大师的德望,要请教治国之道。马一浮推辞再三,最后说道:“唯先儒有两句话可以奉告:唯诚可以感人,唯虚可以接物,此是治国的根本法。”蒋介石不禁愕然。马一浮终不愿为“帝王师”,卷入政治漩涡中,所以很快又将话题转到书院事务上,蒋介石当即允诺,拨款三万元作为建院基金。
3月,教育部主持下,书院的筹委会成立(后改为董事会),成员包括沈尹默、熊十力、梁漱溟、谢无量、贺昌群等名流。马一浮被聘为“主讲”,实际主持书院工作。
书院的地点选在四川乐山县的乌尤山上,离马一浮幼年住的仁寿县不远。这里是岷江、青衣江、大渡河的汇合处。三条大江从不同方向涌来,簇拥着一座青翠欲滴的山峰,面朝乐山大佛,背靠秀丽如屏的峨嵋山,可谓钟天地之灵气。山中有一条小溪,名“麻濠”,后来马一浮的居所就位于溪边,马一浮自号“濠叟”,就是因此溪而起。山上还有一座古台,据说是晋代郭璞注《尔雅》的所在,因名“尔雅台”,这里是后来书院师生聚会的佳处。书院的房屋,暂时借用山上乌尤寺的僧房。
至于书院的名字,马一浮早已想好,称“复性书院”,因为“复性”二字代表了他思想的精髓,他说:
学术,人心所以纷歧,皆由溺于所习而失之,复其性则然矣。复则无妄,无妄即诚也。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教之为道,在复其性而已矣。今所以为教者,皆囿于习而不知有性。故今揭明复性之义,以为宗趣。
“诚 ”在儒家思想中是一种“天人合一”的至高境界,也是每个人天生具有的本性,但被后天的惯习物欲所沾染遮蔽,无法显现;教育即是由知识由外而内的澄明,合以本性由内而外的发显,知行合一,体用一如,使人的本性恢复如初。这就是“复性”二字的精义所在。马一浮是以“复性”统摄理学,以理学统摄六艺,以六艺统摄中国文化,以中国文化统摄西洋、印度诸文化,构成一个“月映万川”般博大圆融的思想体系。
书院招生的消息传出后,因为待遇不错,共有八百多人报名。遴选之下,只招了三十多个学生,教师、教工、杂役,总共六十多人。

1947年4月4日,马一浮与印社同仁方介堪(左二)、马公愚(右二)、吴振平(右一)合影于杭州葛荫山庄、左一为夏承焘
三.一段孤怀谁领得
1939年9月15日,乌尤山上,复性书院举行了朴素而庄重的开讲礼。在熹微的晨光中,以马一浮为首,全院师生一起肃立,向先圣孔子的牌位焚香行礼,然后宾主、师生、同学之间彼此行礼。一千多年来,这样的场景在中国大地上蔚为规模,然而境过时迁,几乎绝迹。现在,在抗战的烽火中,它又如同凤凰一样重生了。观礼的人们不由感慨万分。
开讲礼之后,由马一浮发言,他的第一句话便铿锵有力:
天下之道,常变而已矣!唯知常而后能应变,语变而后能显常。
在清晨的山风中,复性书院的学生们迎来了他们毕生难忘的第一课。
书院的课程设置是马一浮精心拟定的,颇能反映出他思想的构架:首先是“群经大义”,阐发六经的精义,用六艺统摄一切文化;然后继之以“四科”:玄学,义学,禅学,理学。这四者在不同程度上都融合了儒、释、道三教思想的精髓。另外,书院还拟开设西方哲学一科,以期对西方的思想文化也能够有所旁通。
马一浮亲任“群经大义”及“理学”二课,并希望延请其他相关的优秀学者前来讲学,而特别倚重的则是梁漱溟、熊十力两位挚友。他们三人是当时新儒学阵营中最光彩夺目的人物,人称“三圣”,而彼此之间的交情也有十几年了。
梁漱溟是现代史上的传奇人物,早年因与胡适等辩驳中西文化路向不同而一举成名,中年奔波南北,致力于乡村建设,后来更因直谏毛泽东而震惊天下。他于1921年以后学之礼拜见马一浮,此后一直书信往来不断。熊十力与马一浮的交往则更有戏剧性。1929年,熊十力来杭州慕名拜访马一浮,苦于马一浮不轻易见客,又无人介绍,只有写了一封信并附上著作《新唯识论》的手稿求见。信寄出后如石沉大海,几个星期都没有消息。熊十力正感失望时,一日忽然有客造访,通报姓名,正是马一浮。熊十力大喜,却又忍不住说,马先生何不早作回复,让我好一番苦等。马一浮从容道:本当早日奉教,正是因为阁下寄来了大作,我只好仔细读完了,才来拜访。二人相对大笑,从此结为莫逆之交。
但梁、熊都长期在北大任教,而马一浮独居杭州,共处的机会不多。1933年,梁、熊二人在暑假率弟子南下探访马一浮,成为三人唯一一次共同相聚,有人将此比为南宋朱熹、吕祖谦和陆九渊的“鹅湖之会”。当年的合影还摆在案头,现在,马一浮殷切希望梁、熊二位老友同来书院任教,长期共事。
熊十力是筹办书院的元老,本来到书院任教是顺理成章之事,但此后与马一浮书札往来,讨论书院的发展规划,二人意见颇有出入,熊十力同时又接到西南联大的邀约,不由有些踌躇。马一浮再三力邀, 熊十力才下定决心,来到乐山,二人再度聚首。
开讲之日,二人都对学生演讲,对书院的地位、性质、规划和方向等问题阐发了自己的观点,其中多有不合,分裂开始公开化。在熊十力看来,书院应该由国家包下来,扩大招生,资金充足,学生的出路也有着落;马一浮却坚持书院的独立性,不受政府机关的支配,学生宁缺毋滥,出路问题自己解决,书院不是谋出路的工具。显然,分歧是根本性的。
二人一个狂傲,一个狷介,各执己见,互不让步,但毕竟马一浮说了算,熊十力一怒之下,拂袖而去,此时离书院开办还不到两个月。熊十力离去后,梁最终也没有来书院任教。
当年的“鹅湖之会”果真一语成谶,正如朱熹和陆九渊的分道扬镳一样,马一浮和熊十力之间再也没有恢复到以前那种亲密无间的程度。
四.万事车轮直下坡
熊十力走后,千头万绪的问题一时都冒了出来。书院基本上只有马一浮一人授课,不少课程只有搁置。不少学生本来不过想在战乱时期找个避难所,到头来却受不了书院的清苦生活,也不告而别,偷偷溜走,让马一浮大为震惊。同时,董事会一些人把书院当成吃闲饭的所在,介绍亲友来书院任教或读书,而人选往往又不甚合适,马一浮一丝不苟,加以拒绝,自然得罪了不少要人。马一浮的一些思想见解,不少人也不以为然,甚至借熊十力离校的事情大做文章。即使是一些同情马一浮的人士,也觉得他做事过于拘谨,不够通达。明明暗暗的阻力越来越多,马一浮毕竟长期闭门读书,不善处理人际关系,加上对“义理”的执著,和周围的隔阂越来越大。在给弟子的一封信中, 马一浮叹道 :
在今日世法中,乃绝无义理可言。吾所持为义理应尔者,他人视之或以为不合时宜,或竟毫不措意。以素相知爱之久如熊先生,犹不能箭锋相柱,函盖相合,各说各的话,何况余人!
更严重的是资金问题,马一浮本设想可以靠社会捐款支持以维持书院的独立,然而战争时期,根本筹不到那么多款项,最终还是得靠官方的定期拨款。而政府方面,最初说是以宾礼相待,然而实际操作中原定的拨款也常常迟不到位,学校师生,有时几乎要断炊,马一浮不得不再三发电询问,形同乞讨。
勉强支持了两个学期后,1940年7月,马一浮忽然接到教育部通知,要他将书院教师的履历和所用教材“送部备核”,完全是一副上级对下级的口吻。马一浮脾气再好,此时也忍耐不住,于是写信质问教育部长陈立夫说:当初你们信誓旦旦,说“始终以宾礼相待”,今天却又要“送部备核”。书院的教师,是自由学者,不是教育部的雇员;书院的教材,是圣经贤传,不是今人的著作,考核者惟在程朱,折中者惟有孔孟。
教育部的公文,更加促使马一浮下定了决心。终于,1941年5月,马一浮停止授课,遣散学生,结束了他一年零八个月的讲学生涯。后来,这段时期的讲稿和答问辑成《复性书院讲录》、《尔雅台答问》二书出版,成为从不著书立说的马一浮的代表作。
公平地说,复性书院的停讲,固然有国民政府钳制教学、克扣经费的影响,也有战争所带来很多问题,但马一浮本人的不善经营也是一大原因。他毕竟书生气太重,为人端方固执,在并非“人皆尧舜”的现实社会,难免会处处碰壁。当然,更根本的困境在于现代社会体制本身对书院的排斥,正如马一浮所说:若是妥协太多,书院也不成其为书院,还有何意义?直到今天,类似的悖论还困扰着马一浮的精神传人们。
对于书院草草落幕的结局,马一浮其实早有预感,1940年3月,他在告书院诸生的一则启事中就说:“书院亦是缘生法,待缘而兴。缘具则暂存,缘阙则立息。此于道绝无增损。”那段时间,他常常踯躅于尔雅台上,在松风吹拂下,眺望千峰万壑,俯览碧林清江,思考着自己和书院因缘聚散,起灭轮回。…
静树深如海,晴天碧四垂。
一江流浩瀚,千圣接孤危。
聚沫观无始,因风阅来吹。
虫鱼知已细,何物有成亏。(《尔雅台》)
五.乘风归去月明时
复性书院并没有倒闭,而是转为以刻书为主,马一浮希望以此保存一点文化血脉。几年间,书院克服种种困难,刻了《群经统类》、《儒林典要》两部丛书,以经典注疏和儒学语录为主,其中包括不少马一浮担心可能因战火而佚失的冷僻著作。刻这样的书,自然卖不了钱。实际上,由于经费阙如,整个刻书事业是马一浮靠大书法家的身份鬻字维持的。马一浮仍然抱有一线希望:只要书院还在,将来抗战胜利,环境好转,也许就可以延请教师,重新招生,再度振兴。
抗战结束后,马一浮提出,书院要及时东迁,此后恢复招生,扩大刻书,继续发展。1946年5月,马一浮离开了居住了六年多的乌尤山,回到杭州,复性书院也一并迁来。然而重振书院的希望,很快就在内战的硝烟中破灭了。战事连年,经济凋敝,书院不要说扩大发展,就连维持下去也越来越难。终于,1948年秋,由于国民政府经济崩溃,复性书院也正式宣告结束,此时离书院的开始筹建,正好十年。
马一浮重新过起了读书练字的隐居生活,似乎一切在划了一个大圆之后,又回到了最初的起点。当然,这只是表面的,翻天覆地的巨变正在发生。1949年,新中国成立。马一浮不少过去的朋友,不是已经流亡海外,就是正在艰难地“改造思想”。然而新政权出于统战的考虑,并未打扰马一浮在西湖边的隐居生活,还拨出可观的经费,让马一浮能够安享晚年。总的来说,马一浮的晚年生活平静而舒适。
然而马一浮的世界已经仅限于他的书房,窗外已是万象更新的新社会。也许知道真的是“不合时宜”了,四九年以后,他除了写写旧诗以外,再也没有思想著作问世,更不用说当年创办书院,在民间弘扬儒学的理想了。只是偶尔,他会在诗中追忆那个往昔的梦想:
百劫千生示不迁,前尘如梦复如烟。
编蓬采药多年事,云水溪山尚宛然。(《记梦》)
1966年, 马一浮理所当然成了 “封建遗老”、“反动学术权威”,被打倒,抄家,扫地出门,蜷缩在书房中的文化世界也终于崩溃。马一浮毕生收藏的书画大半被狂热的红卫兵焚毁。翌年,马一浮病逝,享年八十五岁。据在场者说,马一浮的死,是平静而从容的。很少有人意识到,一个非常非常古老的时代和梦想也随之一同逝去,不留下一丝痕迹。正如马一浮自撰的墓志铭中所写:
惟适性以尽命兮,如久客之归休。
委形而去兮,乘化而游。
蝉蜕于兹址兮,依先人之故丘。
身与名其俱泯兮,又何有夫去留。
三十多年过去了。又是一个世纪末,又是一个世纪初。又是似曾相识的问题与主义,似曾相识的全盘西化和国学热,似曾相识的教育和体制改革,在一遍遍的轮回中回到从不曾尘埃落定的中国。又是一个注定要在艰难选择间徘徊的时代。只是,我们再也没有了马一浮和复性书院。最后的儒者早已死去,最后的书院早已坍塌,我们,又何去何从呢?
按:各节标题皆取自马一浮本人的诗句。
复性书院为马一浮先生主持创办的一所传统书院。1939年创建于四川乐山乌尤寺。书院从1939年9月份开始讲学,1941年5月停止,前后共一年零八个月。此后转以刻书为主,马先生希望以此保存中华文化之血脉。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马一浮先生返杭,复性书院亦迁至杭州,在西湖葛荫山庄。此后书院改名智林图书馆,以刻书为主。后期则迁到马一浮先生晚年居住之蒋庄。杭州市政府为了纪念马一浮先生,将其晚年居住的蒋庄辟为马一浮纪念馆。
2009年,为改变纪念馆旧有模式,杭州市政府邀请国务院中国国学中心顾问、北京大学中文系龚鹏程教授至马一浮纪念馆参观考察。龚教授提议由市政府委托具操办纪念馆业务之文化团体具体负责运作。
杭州市政府遂于2014年1月起聘请北京大学文化资源研究中心团队负责运营管理。期以马一浮纪念馆为基地,重开复性书院,恢复传统讲学。复性书院现由国务院国学中心顾问、北大著名教授龚鹏程先生主持,以弘扬道化、阐明国学、培育通才、勉成国器为宗旨。

文物网版权与免责声明:
一、凡本站中注明“来源:文物网”的所有文字、图片和音视频,版权均属文物网所有,转载时必须注明“来源:文物网”,并附上原文链接。
二、凡来源非文物网的新闻(作品)只代表本网传播该信息,并不代表赞同其观点。
如因作品内容、版权和其它问题需要同本网联系的,请在见后30日内联系邮箱:chief_editor@wenwuchina.com
月度排行
新闻速递
- 2021年度文物保护示范工程公布
- 李白《嘲王历阳不肯饮酒》诗稿考论
- 习近平: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
- 张同禄80华诞纪念典藏展开幕,景泰蓝《盛世同路》引...
- 为盛世献礼,与第一大党同路!景泰蓝《盛世同路》在沪...
- 国之重器景泰蓝《和平颂宝鉴》入藏敦煌博物馆
- 景泰蓝泰斗张同禄八十华诞纪念典藏展盛大开幕,《盛世...
专题视点MORE
原创推荐MORE
- 文物网培训中心
- 美好时光
- 大家鉴宝—老窑瓷博物馆公益鉴宝活动圆满举行
- 曜变之旅
- 菖蒲河园,一袭釉色染枝头
- 龙泉琮式瓶
- 盛世风袭北京城,金秋月览长安客(下篇)
- 阿富汗珍宝展之:石膏盘上的希腊神话
- 秘色出上林
- 阿富汗珍宝展之:恒河女神雕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