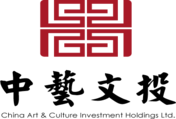与印度纪录片发行人迦琪·森的对话
文/陈韵“西天中土”计划研究员 译/张经纬
魔灯基金会(Magic Lantern Foundation)
魔灯基金会于1989年作为媒体行动团队成立,其目标在于使用沟通工具来促进人权,并使边缘化人群为他们面临的问题发声。在这一过程中,他们逐渐认识到视觉影像媒体(尤其是影像)作为促成社会议题的了解,并开展讨论、辩论的重要性。魔灯的目标在于通过为印度及国外的独立电影提供更多制作、推广、 发行、展览渠道,扩展独立电影的受众与可能性。魔灯基金会是此次“你不属于:印度电影的过去与未来”(西天中土2011)的印度合作方。(http://magiclanternfoundation.org/)
因为“西天中土”在今年的电影项目,我认识了迦琪·森(Gargi Sen)。她的魔灯基金会座落在德里南部一个孟加拉移民的聚居地。她向她母亲租来了这栋她出生和长大的房子的地下室,亲自设计装修变成一个办公室。在这个没有窗也没有手机信号的地方,你并不感到空气凝滞或环境逼仄。这里有办公室、会议室、剪辑室、观片室以及顶天立地的纪录片拷贝。每部纪录片的包装都出自同一位女性设计师之手,墙上贴着大大小小的影展海报和迦琪几十串的影展参加证。迦琪是个短小精悍、看起来富于弹性和能量的女性,本来学习设计,却走上了纪录片的道路。她有一个刚刚从洛杉矶回到孟买三年的弟弟,专业学习电影,喜爱孟买,讨厌德里,且只做虚构片。她的丈夫是一个精通中国革命历史的左派,相信迦琪未必认同的“不断革命论”。她的瘦小的女儿放学回来就往地下室钻。她的母亲和她的四个80岁以上的姐妹使劲热烈地说话(却没有听众),以说话来调侃和克服这个加尔各答移民家庭在过去50多年间所有的愉快和不愉快。就在这样的一栋火热生活着的房子的三楼,我终于在8月的一个清晨抓住了她,让她详细地告诉我魔灯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陈韵:你可以从魔灯基金会的第一年说起么?那是在1989。但草根运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这个和60年代的左派运动有什么联系,和农村、农民有什么联系?
迦琪·森:大概是从80年代开始,当时是因为早期左派思想分成三股主要潮流——一股是研究农村改革,一股就研究环境,还有一股很广泛的潮流是人权。但我们研究人权的时候,是把公民权、政治权,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这些合在一块的一个大讨论。所以这场讨论在80年代早期的印度就开始了。而我们对“魔灯”,是很凭感觉的;我们希望把我们和广大左派、大环境、大的人权这些联系在一起。
陈韵:所以你们就都覆盖了?
迦琪·森:没错,很大的人权。但我们开始研究环境问题就是当作权利问题来看的。所以我大学毕业后,对前路有些茫然。
陈韵:这就是80年代的情况?
迦琪·森:“86、87年的样子。所以我去了个叫萨哈兰普尔的地方,那个地方离德里有200公里。那里有一场很大的运动,是当地人重申他们对森林的所有权。这些人住在喜马拉雅山西瓦里克地区的山脚。运动发生后——大家辩论、谈判,所以我就去了那边看我们能干点什么。我们有个小型计划。我们有一点钱,所以和我创办“魔灯”的同事兰詹也和我一起过去。我们开始研究沟通在社会变迁中所起的作用。问题就是,沟通有没有在社会变迁中发挥作用。
陈韵:你怎么会有这个想法?
迦琪·森:我怎么会有这个想法?
陈韵:因为他们当时还没有开始沟通,对吧。
迦琪·森:我记得,计划很大,所以我就做了视觉沟通。做影像设计之前,我已经研究过沟通和沟通方式。你学了很多技巧,你了解设计哲学,让你了解客户的想法,并阐释出来。这就是设计哲学。不过,我认为沟通哲学有点不同。我认为,沟通哲学从本质上、知识上讲,是一种沟通不同社群、不同话语的需要,并发现你自己该怎么做。而我认为去萨哈兰普尔帮助我们了解了更多。我给你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去那里不是去研究电影或者拍电影。我们只是放电影,但因为没有电,所以碰到了很多问题。我们必须带上工具,接上汽车电池,所有事情都要自己干。但我们要干和影院一样的事情。我们要设计海报,做海报等等。我记得有一天,我们要弄一间海报工作坊。我要找8个村民,我就告诉妇女们我们要弄一间海报工作坊。然后一些村里的妇女就来了。我们说好在这个小镇上见——其实都算不上小镇,那就是个小村子,就让我们能有个地方都能坐下来,一块儿干活。我就一大早就过去,带了所有东西——纸、布、墨水。等妇女们差不多10点过来的时候,他们说,“你知道么?你得和我们一块儿过去,我们要去地方官办公室申请铅皮弄屋顶。”这些房子是泥墙茅屋,我就说,“为什么?”他们说,“因为现在是很干的季节,只要有人吸烟,一点着火了,整个村子就烧光了。所以我们要找地方官要铅皮弄房子,他必须批准。”
陈韵:这算是抗议吗?
迦琪·森:这就是个申请。但就因为这件事,我的海报工作坊没开成。我和这些妇女一块儿去了。你看,就算你有想法,但情况也会变化。意料之外的事情很现实也很寻常。一般我们是按a-b-c-d的步骤,但研究一个大社区的时候就不同了。我们做了很多剧场,我们开始时在一些学校和孩子一起搞工作坊。我们做了很多儿童工作坊,让孩子组织他们自己的活动。这些其实是很小的孩子,大概5-10岁样子,他们会发表对父母酗酒的看法。
陈韵:他们是自己组织的?
迦琪·森:是的,他们自己做了这些海报。自己做了计划,做海报,横幅,组织队伍,在村里游行。海报工坊的效果确实出乎我们意料,产生连锁效应。让我们觉得很有意思。然后们在88-89年那段,发生了关于森林的冲突,我们一般都带着摄像机去记录。89年时,支持我们的组织方问我们愿不愿拍个片子,把这里真实的问题展示给更多人,我们说好,就做了这个片子。这个片子是89年初完成的。
陈韵:你有没有受过拍片的训练?
迦琪·森:我在NID (国家设计学院)的时候学过点摄像基础技巧,但我同事兰詹以前为这个组织在德里拍过反映社会问题的纪录片,所以他实际上比我懂得多。所以我们拍了部叫《因为我们的权利》(Because of Our Rights)的片子。我们拍这个的想法来自人们对森林的权利。还有一个主要原因是当时这个事情掀起的风潮,许多国家媒体介入。他们把这个运动报道成一个法律秩序问题,认为这些人触犯了法律。而我们想说,“不对,这不是法律和秩序的问题,这是权利问题,他们的权利被夺走了。”所以我们拍了这个片子,这个片子变得很出名。片子放映了很多回,发生了很多事情,但最要紧的问题是,我们做片子的钱是自己的,从朋友那儿借来的。所以我们没钱了。我们借设备也要付钱。所以,我们就只好卖电影拷贝,但我们隶属NGO,没有相关授权所以不能卖。这样就是我们创办“魔灯”的原因。
陈韵:为了发行电影?
迦琪·森:为了发行我们自己的电影,赚钱维持工作室。
陈韵:但在80年代后期,社会对纪录片的接受程度怎么样呢?有没有很常见?有没有受屏蔽?
迦琪·森:很难。就算现在,情况还是一样。纪录片其实只在学术圈里放映,因为只有在大学里才能自由放映纪录片。还有就是由欧洲人管理的文化中心:哥德学院、塞万提斯学院、法语联盟、英国文化委员会。除了这些以外,纪录片放映很难,因为纪录片拍摄者还要身兼制片人、导演、发行商。就是这种情况,而且我们还没钱拍片,还要赚钱补贴工作室,因为里面的设备是借来的,所以我们开始卖录像带。我们实际上卖出了录像带并偿还了贷款,并用剩余资金支持下次拍摄。拍摄这部影片是为了开始关于森林权的讨论,所以我们依据对象定价不同:对机构的售价非常高,而草根组织则几乎是免费的。我们也做了一些免费拷贝。由基金支持的NGO则给中间价,所以我们有三种价格,卖了许多电影拷贝,就能办讨论会。
我认为在90年代,大概在89-92年,关于森林政策的讨论在全国全面展开。这部电影也成为讨论的一部分。它对讨论有所帮助,也是我们事业的开始。但在那之后,我们有好几年没拍电影,也没有拍我们现在这种类型的,因为我们已经深入草根,用媒体来研究。我们以电影作为了解社会话语的媒介,从电影中看到印度社会领域中的很多问题。所以我们开始尝试如何把这两者结合起来,然后做了很多训练,让草根人群可以制作他们自己的电影。但到1999年,我们觉得真的很累,因为我们只有这两个人。 
文物网版权与免责声明:
一、凡本站中注明“来源:文物网”的所有文字、图片和音视频,版权均属文物网所有,转载时必须注明“来源:文物网”,并附上原文链接。
二、凡来源非文物网的新闻(作品)只代表本网传播该信息,并不代表赞同其观点。
如因作品内容、版权和其它问题需要同本网联系的,请在见后30日内联系邮箱:chief_editor@wenwuchina.com
月度排行
新闻速递
- 2021年度文物保护示范工程公布
- 李白《嘲王历阳不肯饮酒》诗稿考论
- 习近平: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
- 张同禄80华诞纪念典藏展开幕,景泰蓝《盛世同路》引...
- 为盛世献礼,与第一大党同路!景泰蓝《盛世同路》在沪...
- 国之重器景泰蓝《和平颂宝鉴》入藏敦煌博物馆
- 景泰蓝泰斗张同禄八十华诞纪念典藏展盛大开幕,《盛世...
专题视点MORE
原创推荐MORE
- 文物网培训中心
- 美好时光
- 大家鉴宝—老窑瓷博物馆公益鉴宝活动圆满举行
- 曜变之旅
- 菖蒲河园,一袭釉色染枝头
- 龙泉琮式瓶
- 盛世风袭北京城,金秋月览长安客(下篇)
- 阿富汗珍宝展之:石膏盘上的希腊神话
- 秘色出上林
- 阿富汗珍宝展之:恒河女神雕像